地域的观念,在现代印人的心目中已渐渐淡化,但一旦某地出现一个能够左右当地印坛的人物(注:有时与这个人物的实际篆刻创作与研究水平无关),则相应地会形成一定特色的地域风貌。至于流派篆刻的形成,似较自然,它的地域色彩反而不甚明显,如我们经常提到的韩天衡、王镛、石开三家,均系自然成形,其影响所被并不局限于自己活动的本土,有的甚至在外地影响更大。因为学习他们篆刻或受其印风影响的人,大多是通过有关出版物上发表的作品私淑而成,与本人可能并无直接的师承关系。从这个角度看,当今篆刻界所呈现的地域风貌或流派特色,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等,与明清时期并不相同。随着篆刻界信息交流媒介的发展,篆刻创作的地域风貌与流派正在走向浑融和调和,这种趋势最终将消除因单纯流派及地域风貌近亲繁殖所带来的雷同,并为篆刻家主体精神的大力弘扬和个性发挥打下良好的基础,其意义无疑是积极的。
在曾经是中国篆刻创作与研究重镇的上海,老一辈以工整浙派印及赵叔孺圆朱文、满白文印见长的篆刻家,在全国乃至于沪上的影响与地位,正日渐减弱与下降,继之以韩天衡、刘一闻等风格各异却又极具海派特色的全新印人。特别是韩天衡,以他较为全面的修养和“文革”后先出之利,在上海及全国形成了一大批很难彻底跳出其篆刻中潜伏习气的追随者(这种“习气”对韩本人而言,乃是他印风形成的前提,且仅仅是潜伏而已,但对于没有韩所具有的篆刻功力和修养的追随者来说,就真是习气了),他们的篆刻创作几乎一开始都以韩氏篆刻所特有的字形大幅度扭曲、刀法极力外露霸悍的面目出现。后来,又大多在韩氏的要求与呼吁下转向工整、平实、刀气十足的印风,即便如此,能够在今后创作中跳出先前业已形成的“韩流”的追随者,已经不多。引人注目的是,在韩天衡篆刻的追随者中,虽极少有超过乃师的力作出现,但在一系例较权威的综合性书展中,这些作品却获奖频频。个中原因,想来是这种将篆字扭曲变形且充满镌刻气的篆刻,较能迎合对篆刻略知一二、以书法见长的展览评委。因此,“韩流”(并非是指韩天衡本人的创作)及其意义的积极与否,看来还需待些时日方能够彻底分清。
相比之下,刘一闻和徐正廉的篆刻风格,追随者似乎不多。这两者之中,一典雅细腻见长,一则极尽开合变化。或许是由于年龄、底气、迟出,或是其他一些难以说清的原因,他们在全国范围内的影响,比之在上海要大许多。话又说回来,当今上海印坛中最有特色和最具生命力的作品,还是韩天衡在70年代末期所创作的一些精致且字法变化较为自然的小印,他的这批作品,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显其英雄本色!至于近几年来,各方面条件都很优越的上海,很少出现出类拔萃且有全国影响的青年篆刻家,窃以为可能同上海相当长时期以来将篆刻的普及教育走入拟古保守的误区有关。当然,这仅仅是我的直觉,未作详细的调查,仅存此一说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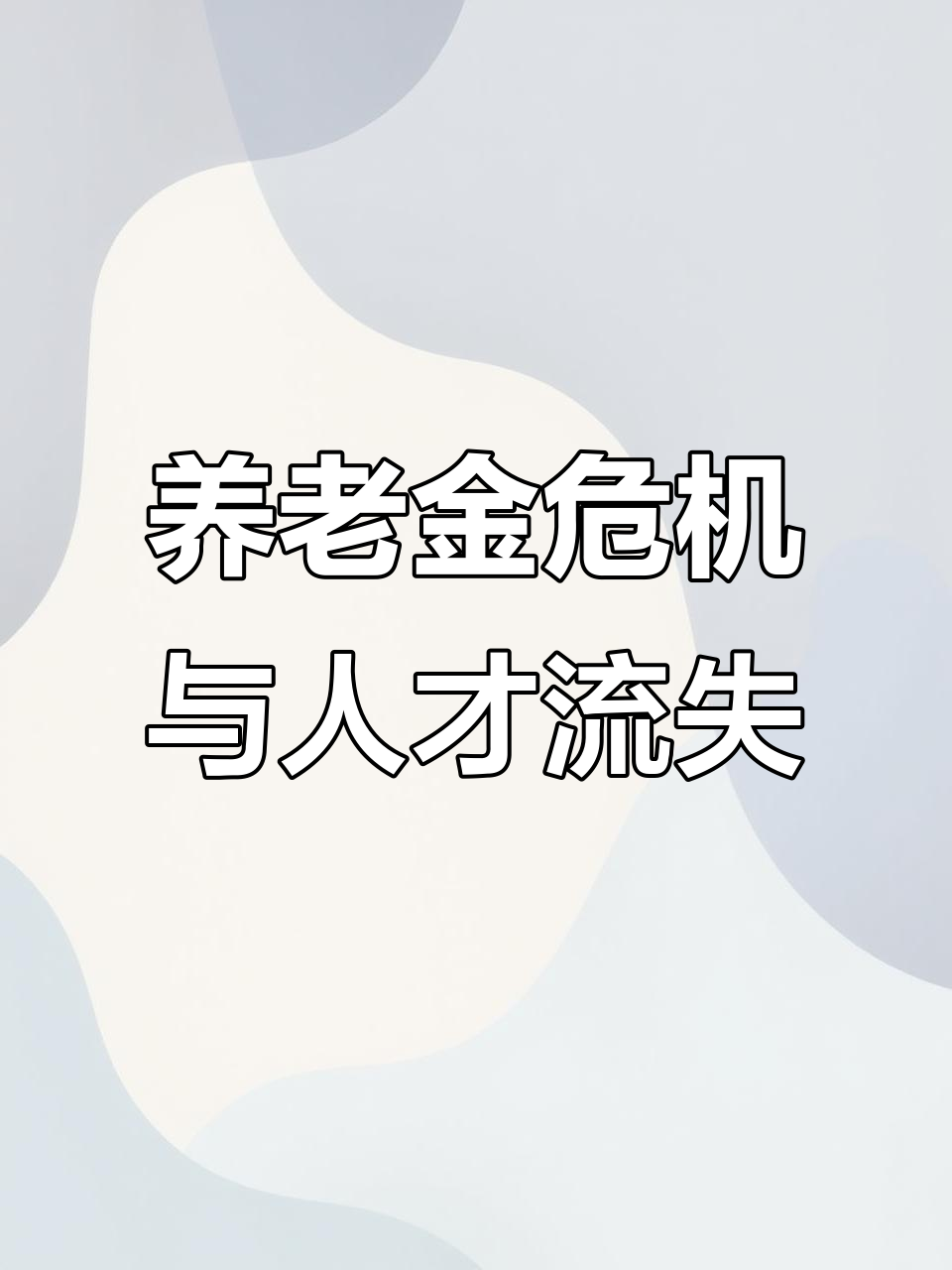
北京的篆刻,以王镛80年代中期在印坛崛起为标志,形成了覆盖全国、带有明显王记特色的“王派”,但受王镛影响或同时以苍茫率意的风格作为自己创作追求的姣姣者,大多仍在北京一带,如崔志强篆刻的犷健、陈平篆刻的厚朴等,均带有自己的特色。现在“小刀会”中的几位青年印人,则更是以烂漫甚至近于荒诞的面目和用刀,令当今印坛为之一振。但这样的作品所能达到的高度,似乎全凭悟性与灵气,而灵气与悟性的偶发性、短暂性,决定了他们却并不能一辈子以此引导自己的创作,因而照此下去,很难有大的发展与回旋的余地。值得一提的是,熊伯齐篆刻中为数不多的以陈师曾刀法和线条韵味出之的仿古小印,可谓是近年来对古玺借鉴与出新的最成功者之一。另外,刘恒的篆刻,亦以其颇为得当的残破功夫和对汉烂铜印的借鉴,为当今印坛开一面目!
四川的印风,令人不尽满意。按理说四川人的泼辣,人所皆知,篆刻依然才是。但或许是出了个在全国有一定影响且充满学究气的徐无闻,又作研究生导师之故,因而在今人心目中,四川的篆刻大多极工整细丽之能,面目较为单一。在韵致方面,似乎也不及上海老一辈篆刻家。
江苏的篆刻状况又怎样呢?笔者生在江苏,较为清楚。以江苏特别是苏南一带所特有的文化底蕴看,江苏的印人之中出几个能在全国领几年风骚的篆刻家应属不难。但时至今日,能够称雄全国并取得与韩、王、石等相鼎足的人尚未出现,有一定全国影响的篆刻家也不很多,并且其在全国篆刻界的影响力和印人心目中的地位,正日渐减弱与下降。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我的分析是在于文化底蕴的深厚与当今文化氛围的冷淡和人们心目中艺术地位的下降之间所形成的、无法调和的矛盾冲突。在这种矛盾冲突面前,篆刻家的心态对于其篆刻艺术的创作来说是致命的。首先,他们大多都极想跳出过分深厚的传统的束缚和已有的小圈子,但在这个过程之中,又往往无形中深受传统中保守与内敛的负面影响而不能自拔,靠别人和某个什么机构的帮忙则更是无从谈起。除了人人都是“文人”所导致的“文人相轻”人际关系的冷漠和文化部门有限的人头费用无法进行他用以外,更主要的是因为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当今薄弱的人文环境,冲淡了人们对艺术,特别是对艺术中新思维,新的表现形式等的感悟与兴奋的能力,因而在江苏的篆刻家中很少有以积极主动的行动来证明自己的存在。而搞展览、出作品所必须的赞助,在江苏又远较那些经济相对不发达地区来得困难。其次,是篆刻家社会地位相应的不高和生活水准、居住条件的相对低下(在江苏以篆刻创作成就受到政府或企业较大奖赏的可能闻所未闻),又使得他们的内心深处的自卑感和压抑感,无法在艺术创作的冲动和快感下得以消解。因此,表现在作品的创作上,都似乎有日趋僵化,如发不出的馒头一般的现象。要解决好上述问题,使江苏的印人特别是青年作者的创造力量得以最大限度的发挥,以便在全国范围内形成江苏应有的气候,我以为靠天、靠别人是不行的。江苏的篆刻作者们所需要的是要尽快地解决好因上述矛盾导致的心理障碍与心态上的不平衡,跳出并打破各种有碍于艺术家个性发挥与创作创新的怪圈。于此,广西南宁诸中青年印人近年来所表现出来的健康进取心态和行动,无疑可作为一种值得借鉴的楷模。当然,江苏黄惇、马士达等中年篆刻家,以他们十余年来的创作和研究成果,在全国篆刻界取得的地位和造成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
福州石开的篆刻所具有前卫性,使得他的影响在经历数年之后还有再进一步延续的可能。但窃以为,石开对篆刻界的最大贡献,倒还不是他独到的诡怪印风,而是在于他在一系列篆刻活动与行动中体现出来的、在当今书法篆刻界很少见的、独立不阿的人格力量和洒脱的艺术家气质。石开的篆刻风格被人所接受,首先是在相对保守的上海,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在福建,出现受石开篆刻影响的印人,似乎只是近几年的事情,这从一个侧面验证和说明了并非正常的、当今许多地方中青年书法篆刻家“墙内开花墙外香”的现象。
辽宁、山东等地的篆刻,近年来也初步形成了一定的地域特色。但由于这种特色尚不显著,特别是缺少有全国影响的领衔者,使它们在全国篆刻界还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
在篆刻创作与研究,以及篆刻新人的培养与展览组织工作做得都很好的河南和浙江,其发展情况也不一样。前者以李刚田、查仲林、许雄志等人为代表,在开放、外向的借鉴和交流中,逐渐形成了风格与面目各不相同但内在联系明显的创作群体,并产生了一定的全国性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河南近几年的篆刻发展同明清流派印章中以地域命名的流派,非常相似,故谓之为“豫派”或“河南派”如何?相比之下,浙江在篆刻创作与研究上的整体优势尚未能最终发挥出来,这种情况可能同浙江篆刻的组织者对篆刻新人培养与成长所采取的方法与对策有关。可以相信,如果浙江的篆刻能够以浙江流传有序的浙派传统和西泠印社巨大的社会影响力为依托,并能够以开阔的胸襟和气量去接受新的篆刻观念的挑战,是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在篆刻创作与研究上所达到的高度领先于全国的。恕我直言,当今浙江的篆刻,尚未能够发挥中国美术学院书法专业在篆刻教育方法上的独到见解以及西泠印社作为出版、组织和商业机构在浙江的巨大优势。换言之,是这种优势在利用上出现了并不合乎艺术创作研究及社会发展规律的情况。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

颇值一提的是,近年来广西以陈国斌、张小弟为首的中青年印人,以全新的面目和人们颇不以为然的行动出现在当今印坛。笔者曾有机会同他们中的一人作过较为深入的交谈,初步得出的结论是他们并不缺少常人所言及的个人艺术修养与必要的艺术氛围。虽然当地的文化底蕴要较江南差许多,但坏事有时在人的主动努力下往往可以转变为好事,因为在他们身上,体现出了当今篆刻作者少有的艺术家气质和锐意进取、不以古人名人唯是的,然而却是理智的创新与求变的勇气。我以为,他们观照各种书法篆刻教育中采用的行之有效的简单手法,对类似于江苏这样的地方而言,是有一定启发意义的。